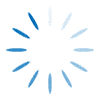第2786章 空樽
我……可以活?
戏相宜的脑海里,关於机关的种种奇思还未散去,对於当下的思考,像生锈的铁齿轮,艰难地转动。
戏命……怎么了……
我的家……
最后才是那句——“为我制器”。
灵识如受雷殛,骨骼里发出惊响,戏相宜猛地抬起头来,隨著短髮扬起的,亦不知是汗是泪:“不!”
她大声反对。
仿佛只有用尽全力的吶喊,才能表达她的抗拒:“真正的创造不能在囚笼里诞生。我绝不为你制器,我只为自由的灵感而创造!”
鉅城的鉅,更是规矩的矩。
在那座坚硬如铁的城市里,她戴著镣銬创造,於无处不在的规训下,在目之可及的壁垒中,重复著那些枯燥的机关学知识,直至全部烂熟於心。
崇古派將她逐出鉅城,反倒是放羽於林中。
在顛沛流离的现世,她看到星光灿烂。在无日不战的妖土,她看到文明的火。
来到神霄世界之后,她真正感受诸天之奇,得取诸意之新,每天都在诞生新的灵感,拥有无限发扬灵感的自由。
是的。她身心抗拒於此,傀儡艺术的创造,不应该遵循他者的命令。她绝不能將她的创作,重新归於笼中。
鼠秀郎五指一合,面涂油彩的假小子,即被扼住脖颈,悬在空中。她的吶喊也被掐灭在喉咙间,脸上的油彩很有几分混淆。
这一切甚至是隔著机关室来进行!
这是她的灵感小屋、武备仓库,也是她精心设计的机关堡垒。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,並不能对她提供半点保护。
“你所说自由的灵感……到底是什么?”
“在这个强权定义一切的世界,焉知你的所见所闻,不是上位者的书写。”
“那么被他者授予的感受,也是你的自由吗?”
鼠秀郎的嘴角泛起一丝冷嘲:“活在羽翼下的小女孩,拥有顶级的传承,受著时代的托举……人族贪掠诸天,你家又贪掠谁家!生下来什么都有了,在鲜血洗过的神霄世界依然天真懵懂,你也说自由?”
他立身在青石铺路的后院,感受著整座青瑞城的不安和孱弱,將目光倾注在戏相宜的小脸上。
“並不肩负责任的人,你確实是自由的!”
他覆手而盖,戏相宜直接被按砸在地上,发出轰然声响。创造傀儡的人,也如傀儡般被任意摆布。
隨地散落的机关零件,是戏相宜进行到一半的创造。她娇小的身体,被骨骼的哀鸣所淹没。可身体的痛楚根本叫她麻木,她蜷缩著,扭曲著,却呆滯的、近乎本能地抗拒:“我不……绝不答应!”
“嘖——”鼠秀郎冷漠地摇了摇头:“你的反抗让你的灵魂生辉。但这种不懂事的坚决,是不是因为你从来没有感受过痛苦呢?”
“明明是可爱的女孩子,有漂亮的五官,却在脸上涂得乱七八糟,穿得也不伦不类。”
“你活得真是悲剧啊。”
“从来没有人教你怎么打扮自己吗?”
san josesan josedating
他伸手一招,便在火光四溅之中,按灭了机关室里层层即要爆发的机关,將戏相宜从机关室里取出,像在半透明的货匣里,取出一个易碎的陶偶——
“来,我为你梳妆!”
他要给这女孩儿抹上胭脂,要把那中性的短眉修成柳眉,要在她的额间贴上花黄。要给她穿好看的裙子,短髮要蓄长。
他懂得什么是美丽。陶塑泥偶,亦不免任他打扮。
但这时有火。
炙热的如同被煮沸的火,在鼠秀郎的身前腾焰而起。
急剧升高的温度,叫空间都有几分扭曲。戏相宜几乎窒息的那张脸,也在扭曲的空间里变得隱约,被推得遥远。
鼠秀郎微微垂眸。
扑倒在他脚下的那具千疮百孔的尸体,从每一个伤疮血洞里,翻卷出黑色的火焰!
在他的妖眸之中——那黑色的火焰不止是火,分明是无数黑色的蚂蚁,如同地热涌出乾涸的山体,就这般衝出残躯,翻滚匯聚为黑色的烈焰。
竟都是墨蚁!
能够吞金嚼铁、噬元食力的墨家造物!
墨蚁的口器共鸣出冰冷的声音——
“戏相宜只忠诚於她自己。她的灵感是自由的,她的美丽也是。”
“浓妆也好,淡抹也好。”
“总是相宜!”
“用不著你来为她梳妆,用不著你自以为是,指手画脚!”
密密麻麻的墨蚁彼此咬噬著,匯聚成清晰的人形,在那具残躯之上,摇摇晃晃地站起。黑光一抹,霎归为戏命的模样。
他抬手一割,將遥远的桎梏斩断,令得已经被他推远的戏相宜,缓过劲来,可以大口地呼吸。
而他直视著鼠秀郎,眸光冷冽,如寒霜之刀:“你究竟是被摆布了多久,才这么热衷於摆布他人。天生万物以自由的贵重,没有人是你意志的延伸。你生活在痛苦里,才会认可那种痛。你一定是你自己最厌憎的那种人!”
一霎蚁潮铺天!
一眼看不到头的黑潮,仿佛结为戏命的长披,隨他招展。一蚁食元,百蚁噬空,千万蚁,绝灵跡。
戏府之中,忽然暗了。
虽然长夜未至,一室之內,已顛倒乾坤。
秘技·乾坤逆。
与传统的道法不同,此术並不藉助道元,而是把墨蚁当做施术的基础,通过墨蚁噬元食力的特质,对所处空间,进行客观上的改变——就像把一个圆饼,啃噬成不同的形状。
呼呼呼呼!
被不断推远的戏相宜,大声地喘息。
看到戏命重新站起的这一刻,才能醒神。当那种呆滯的状態破碎,她才明白自己一开始的呼吸困难,是因为什么样的痛。
才看到自己的心,明白自己为什么执著地对那一句“为我制器”大声说不。
本以为那是自己最不能接受的地方,所以才本能地抗拒。
其实真正不能接受的,是本能已经逃避去想的那些!
她不能接受戏命的死。
不能接受自己失去这个“家”。
她无法接受那么仓促的告別,完全不可以触碰那样的痛苦,只可以吶喊自由。
而戏命从尸体里起身,再次唤醒这心情。
“瞎了你的眼了……”
鼠秀郎在暗下来的庭院里,莹润有光。冷眸垂视著,竖掌为刀,斩劈蚁潮:“竟然看不出来我是一个妖族。我是天生地养的贵胄,可不是你们这种下贱的造物。”
刀光如电游走,蚁潮翻卷不休。被抹杀一浪,又一浪扑至。
戏命亦在蚁潮中踏浪而近,手上墨蚁也聚成一柄墨刀,掀起墨潮如开屏,迎面对斩——
【快走!去泊头城,转道中央天境!】
隱秘的意念为墨蚁承载,像是一个浪头將戏相宜推远。
戏命自己却拦在鼠秀郎的身前,如墨的长披试图遮掩身后的所有:“妖族和人族有什么不同吗?痛苦的经歷是同样感受,恶毒的本性总是相通!”
“下贱的是你丑陋的样子,不是因为你在泥潭中。”
“光明正大地杀了我!”
“折辱弱者算什么本事!?”
与当下任何一位机关师都不同,戏命竟是以墨蚁为他的机关术基础!以之为傀,以之施术。
这是体系的变化,而不仅是秘术的不同。就像仙术之於道术,就是创造性地以术介为施术基础。
但鼠秀郎並没有在意这一点。
人族的创造已经太多,人族的天骄早就让他们从震惊到绝望再到麻木。
他在意的反倒是戏命的抗爭本身。
其实是欣赏的。
他当然看得到一个人为另一个人的牺牲,明白戏命的勇气为谁而点燃。
但人族之勇者,是妖族之大寇。类似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,同样的悲剧在妖族不断重演,他的怜悯不应给予异族。
且他甦醒在金宙虞洲……这消息绝不能外传。
至少在他杀死宫维章之前不可以。
“是啊,大家没有什么不同……”
鼠秀郎的眸色略有沉黯,合握五指而成拳:“我不会折磨你——这是我最后的尊重。”
他横平地一拳直轰!
一拳断墨刀,一拳击穿戏命的心臟。
他的拳头在穿过戏命的身躯后,又击穿了蚁潮,分指为爪,要將那已经被推远的戏相宜取回!
可他的手臂却僵直。
他的手臂竟然被钳住了一个瞬间!
他精准控制力量,本该完美碾杀对手,不造成一丝一毫的浪费。
可被他一拳击碎的戏命,竟然还活著。其人撑著胸腹之处巨大的空洞,竟用双手死死地钳住了他!
这掛在他手臂上的人类残躯,所谓的金躯玉髓,竟然爆发出更高层次的力量……远胜於神临,洞察世界本质,洞真境的力量!
这股力量爆发得如此突兀,事先不察而起如山火。若非鼠秀郎乃一代大圣,曾据诸天之巔,都险些叫他脱去。
鼠秀郎漂亮的妖眸里,终於有了异色:“在我收集到的情报里,经营『戏楼』的戏命,只是神临。”
san josesan josedating
“在我的感知里,你也只是神临。”
“就像刚才我明確感知你已经死了,你仍能站起来。太怪。”
他的手臂从戏命的心口退出,驀地掐住了这人的脖颈:“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……竟能骗过我的感知?”
一缕妖异白焰,游窜於蚁海,大片大片的黑色,被白焰抹空。
密密麻麻的墨蚁,终究不是无穷无尽。
戏命许多年的积累,在一个呼吸之內被打空。墨海退潮了!
被墨潮悄然推远的戏相宜,仍未推出这宅院。
全方位的压制,一丁点机会都不给。
戏命被掐举在半空,被掐灭了所有后手,不得动弹。但还死死地盯著鼠秀郎:“你想知道我的秘密?这是墨家几十万年不曾示人的核心隱秘!放了我妹妹,我会让你满意。”
“多么了不起的隱秘,会在你这样的墨家弃徒身上?我很好奇,但杀了你我自己会找答案。”鼠秀郎的手慢慢合拢,如握时沙。
他掐著戏命的寿数,亲眼看著它如时沙消逝。要在这个过程里,看清楚戏命当死而未死的秘密是什么!
即在此刻,刻著龙凤瑞兽的大门,轰然洞开。
以蓝色傀线织成的“戏府”二字,这时闪烁红光,在做最刺眼的警告!凤鸣之声也变得尖锐——
“恶客登门!恶客登门!”
一队甲士鱼贯而入,以最快的速度占据前院关键位置,並始终保持阵型,向內院推进。
为首的校尉高声呼喝:“我乃弘吾军执旗校尉欒季,奉绣衣郎將之命,前来清治青瑞城匪患,確保神霄中立之地里的人族安全。戏老板!你怎么样?”
人族和诸天联军都会在中立地带活动,普遍也尊重神霄本土生灵的治权,不会动不动开杀。这也是戏家兄妹在这里做生意的基础。
欒季是个精瘦的汉子,握刀稳,中气足。他身后足足五十人,都是大荆锐翎士……绝对的精锐小队。
宫维章留下这样的一支队伍,名为清治青瑞城匪患,实是一种警示。既是警告玉蟾山那边的蒋肇元,不要再做不相干的事情。也是警告戏命,叫他该走的时候就赶紧走。
当在此时,成为破局的力量。
戏命並不知晓府中这个妖族绝巔是谁。
但对方既是潜来青瑞城,定有不可告人之目的,一定要想方设法隱藏自己。
只要把动静闹起来,对方將不得不避退。
而这就是戏相宜逃脱的契机!
所以他在抗爭对手的同时,指挥墨蚁咬噬府內能源的关键节点,以机关宅院的整体脱节,引动了戏府大门的最终告警。
留守在此的欒季,有一贯的荆国军人的果决,察觉到戏府的变故,立即破门而入。
鼠秀郎侧回头,眸中红光一闪——
妖法·憎血!
“这是什么!呃……啊!”高举大盾率先探入內院的甲士,体內鲜血忽然暴动,自內而外,轻易地扎穿血肉皮囊,击破鎧甲。將他悬钉在空中,像一颗生长於此的血色刺球!
血噗之声不绝於耳。
以战阵姿態衝进內院的五十名荆国锐翎士,连同带队的欒季一起,全都被自己的鲜血扎穿,虚举在空中!
san josesan josedating
欒季倒是还没有立即便死,鼠秀郎冷漠地看著他:“欒季?”
“执旗校尉是第三级尉官,已经达到將官的门槛,可你的军事素养实在令我失望。上官难道没有教你,面对能力范围外的变故,不要擅自做决定?”
“我已给足了机会,儘量只体现洞真层次的力量,儘量拖延时间。就是为了等你回去匯报,把你们的郎將请来——你却自己就带著人衝进来了。”
“这叫我怎么办?把你放走也太刻意了。我还能钓到血鱼吗?”
戏命的一颗心直往下坠。
眼看著朝夕相处的弟兄瞬间惨死,欒季目眥欲裂:“在正面战场溃不成军,你们也只能玩这种偷鸡摸狗的把戏了!堂堂绝巔来杀小卒,你不会有好结果,一个荆人必要有一百个妖族来陪葬!”
鼠秀郎在等他自己生出假讯骗来宫维章的主意,可这小小的执旗校尉,眼中好像只填著恨。
“从军者当有其责,你带著这么多人死在了青瑞城,不打算回传一丁点情报吗?”鼠秀郎提醒。
“相较於我浅薄的耳目,我的战死是更清晰的回信。”欒季怒目高喊:“大荆必胜!”
嘎巴!
上涌的鲜血聚成尖刺,刺穿了他的脑袋,却又撑住他的脖颈。使他的头颅侧歪,像一颗掛在树上的大果。
在他彻底死去后,鼠秀郎才道:“你的忠勇我认可了。没关係,你的郎將,我会上门去找他。”
满院血刺如林,戏府以红为新景。
鼠秀郎的手还在慢慢收拢,虽然当下的目標是宫维章,但对戏命的兴趣这时也非常浓烈。
求知是强者的阶梯。往小了说,视野的拓展关係到他自己的未来。往大了说,一条全新的道路可以填充妖族的底蕴。
“我帮你制器!”油彩糊了满面,像只小花猫一样的戏相宜,带著哭腔地喊。
被戏命送走,又被鼠秀郎抓回,又被送走,又被抓回……她太孱弱了,所以根本不能自主。
她总是没有自由的。
从小就被关在小小的房间里,只有一部部砖块一样的厚书,垒成记忆里的高墙。一页页地翻过去,她也就慢慢长大了。
可是长大了也只是被关在大大的鉅城中。
那次带著【明鬼】出任务,其实是她第一次出远门。离笼的小雀儿,陪著铁老头,將一只骄傲的凤凰,抓回笼中。
这次任务永远地改变了人生。
天工真人铁退思,是戏命和钱晋华鉅子之外,陪伴她最多的人。
后来钱鉅子死了,铁老头自杀了。
她的世界很简单,可她並不愚蠢。
她离开鉅城之后之所以存在自由,是戏命儘可能地为她张开羽翼!
现在她像一只笼中雀,可怜兮兮地被囚禁在空中。无形的力量压制了她弱小的反抗,她不觉得自己可怜,只是看到戏命腹部的巨大的空洞,感到心臟被揪紧的痛。
被掐住脖颈的是戏命,可呼吸不过来的是她!
她並不理解这种复杂的心情。
可她情愿交出自由,情愿放弃灵性,她可以扼杀自己的创造性。从此身在傀线,做模具里的作品。
san josesan josedating
“我可以帮你制器……”她抽泣著说:“做很多松鼠。不要……不要……”
鼠秀郎沉默地看著她。
这个小女孩儿好像並不明白,从头到尾让她听话制器都不是重点,那只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等宫维章过来,隨便找的一个理由。
可正因为她连重点都搞不清楚,这种决心才叫他动容。
曾经那些亲眷为了保护他而一一死去,哭著笑著强装镇定的那些脸,那些真心也像今天一样……让他心中流泪。
可是怎么办呢?
他笑起来:“怎么办啊……我现在也这么恶毒。戏命说得没有错,我也变成自己最厌憎的那种傢伙。”
笑容一点一点地收下去,他看著戏相宜:“我可以放过你,可以把你放回妖土,任你制器或者不制器,给你有限的自由……但我不能放过他。抱歉。”
戏命身上的秘密,是他必须要探索的。这是他作为妖族绝巔的责任!
他的五指猛地一握紧!
“告诉我你是怎样死去……又怎样活著!”
“……唔!”戏命在鼠秀郎掌心拼命地挣扎,他的挣扎並不是进攻,而是回头看——他似乎想要最后看戏相宜一眼。
纤长的五指就此合拢。
啪!
戏命的整颗脑袋,就这样炸开了。无头的尸体坠落,离体的头颅如爆竹。
鼠秀郎的瞳孔微缩:“这是什么?”
颅骨四碎,脑浆迸飞。
那包裹著脑髓的密布精密血管的软脑膜……铺开来像一张泡胀的纸。
其上竟有字!
上面书写著——
“洞真之限”。
这四个道字古拙藏锋,有妙不可言的道韵。
但分明是拓印而来,而非谁当场手书。
谁在戏命的头颅深处,留下这样的文字?这个戏命…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?
刺~啦!
这张如泡胀的纸张般的拓印了道字的软脑膜,在空中被撕开。
咔咔咔!
咔咔咔咔!
自鼠秀郎掌心坠跌的无头尸身,竟然发出齿轮转动般的连绵声响。一股强大而又鲜活的气息,突兀诞生。
空气中游离的能量,疯狂向这具残躯聚集。
残躯的双足落定在青砖上,稳稳站住。整座庭院里无数机关造物,在这刻全都黯灭。
唯独这具残躯的躯干璨放炽光,自脊柱部分旋升起金属般的翼弦,迅速编织成头颅的形状,而后辉光凝实,结成颅门,结成清晰的戏命的五官。
戏府在此刻陷入绝对的死寂,全新的戏命却粲然见辉。
戏相宜愣愣地看著这一幕。
眼前这些东西她都认得,是灵枢,是脊螺,是翼弦,是玄儡……
可这样的戏命,让她好陌生!
“傀儡!你竟然是傀儡!”
鼠秀郎一时惊声:“原来墨家的启神计划,不止造出三尊洞真!”
san josesan josedating
“你这一尊,比那几尊都要灵动!什么【天志】【明鬼】……”
说到这里,他怔了怔:“说起来从来没有人见过【非命】。墨家从来不掩饰这尊傀儡的存在,但在我们所掌握的情报里,它一直在鉅城深处,从来没有真正放出来。据说是为了『非命』的精神,非命运波折不应,非宗门存亡不出——”
“是的,我就是『非命』。”
戏命眉如冷刀,直视鼠秀郎,这一刻他的气息飞速拔升:“机关术的最高成就,启神计划所留下的第三尊。”
“不对,作为千机楼的管理者之一,你有明確的成长轨跡。从內府到外楼再到神临,都有清晰的节点,有很多人看到。”
鼠秀郎不可思议地摇头:“一尊具备成长性的、活著的傀儡?”
这一刻他意识到,神霄大世界於冥冥中所提醒的因果,或许並不在於宫维章,而是近在眼前!
或许这才是他坠落在这里,戏氏兄妹也在这里入宅为家的原因……真正的天意如刀!
“我是启神计划里的第三尊傀儡,並非真正拥有成长性,而是拥有五种形態。”戏命迅速地重建自身:“你真的很谨慎。哪怕是处置区区一个戏命,在动手之前你也搜集足够的情报……”
“但即便搜穷有可能潜来神霄的妖族绝巔,也没有你的信息存在。我怎么都想不到你是哪一尊。”
“或许因为我只是傀儡吧。”
他的声音有几分可惜:“我只能搜穷已知的信息,锁定確然的结果,无法获取未知的灵感。你当在那些『不可能』中。”
“但这里是神霄,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世界。”鼠秀郎说。
“是啊……无限的可能。”戏命喃喃重复,似乎陷入某种认知的困境中。
鼠秀郎注视著这具傀身的细微变化:“我是依託於神霄世界而重构的绝巔,此生限定在这里,出则墮境。交换答案吧!既然你只是傀儡,那这以墨蚁为基础的法术手段,又是何来呢?”
“它並没有那么伟大,不足以形成新的墨术体系。只不过是创造者特意留下来的一套新术,烙印在我的神天方国里,用以掩盖我的非真。”戏命说。
鼠秀郎確定他所说的並非谎言,心中的危机感稍得缓解:“所以……你的五种形態是哪五种?”
“如你所知,內府、外楼、神临、洞真,以及……”戏命的眼眸骤然璨亮,这一刻他似乎解开了长久以来的制约——
“当下这未完成的绝巔!”
他的身体在他飞起的同时,就已经开始裂解,一小瓣一小瓣如飞灰跌落。
可他的力量如此澎湃,是真实不虚的绝巔,以拳对掌,与鼠秀郎半步不退地对轰!
都说是钱晋华那殞身的一跃,完成了墨家绝巔级傀儡的创造。墨家也以此功德,得到诸方默许,占据一个阎罗尊位。
直至今日才叫人知——原来当初饶宪孙的启神计划並没有完全失败。至少名为【非命】的这一尊,可以在自毁的时刻,有短暂的绝巔层次的爆发!
这一刻整座戏府框地为圆,其中如混沌初开宇宙演化,两尊绝巔无限制地出手。
尤其是戏命,只攻不防,每一拳都奔著同归於尽而去。
一地青砖成齏粉,而后粉尘也轰无。
整座戏府都已经被推平,两位绝巔的战场,是一个光溜溜的圆。
若非鼠秀郎有意收拢力量,戏命也不肯波及戏相宜,双方有生死划线的默契。整个霜云郡都不能存在,金宙虞洲都有可能被击沉——
这还是神霄大世界屡得跃升的结果。
风捲云开后,鼠秀郎仍然傲立原地。
已经断了一只手臂的戏命,连轰三拳——
命限!演穷!算绝!
此三式都出自墨家大圆满拳术——《天演拳》。
號称“穷极算力,究尽天工”。
是推演到演算所能抵达的极限,升华到机关所能抵达的尽处。
除了【鬼斧神工】的舒惟钧之外,从来没有人能把这三拳轰出圆满。
甚至即便是舒惟钧,在“算绝”这一式上也有缺憾。
原来这是专门为绝巔层次傀儡所创造的拳术。
也只有真正的天工造物,能够詮释这样的拳。
鼠秀郎一口鲜血喷出来!
但只抬手轻轻地抹去。
“確实只是傀儡。虽然远胜於【明鬼】在洞真层次的表现,也中规中矩地体现出绝巔力量,终归缺乏足够的创造性,不能演化真正走到超凡尽头的圆满。”
他难抑悲观地嘆声:“你都能跟我斗到这般程度,饶宪孙令我生畏……他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者,古今第一的机关大师!”
他鼠秀郎是妖族大圣!诸天万界最强的那一层。
可戏命只是一个傀儡,创造他的人已经死了几百年。
这样的两个存在,竟然能够成为对手,在这神霄世界的某个角落,打到这种程度。
这样的人族,究竟要怎么去战胜?
饶宪孙在人族不算耀眼。
继其遗志、一手挽救墨家的钱晋华,后来完成的绝巔傀儡……在冥府立神的【非攻】傀君,又是什么样的强度?
轰!
戏命双臂皆断,下半身也不復存在,只剩个半身被轰远,跌落在戏相宜身前。
鼠秀郎轻轻地一拂袖,迈步而前:“小女孩儿,我承诺过不杀你,但你和这具傀儡,我必须带回去。抱歉——”
刷!
一道惊电般的刀光,炸耀长空。
来者毫不掩饰力量,这一刀劈开了整座青瑞城。
刀裂城池而不伤其间生灵,劈斩至戏府,才骤然凝练——闯进两位绝巔的战场,刀光如天瀑倒灌,倾落鼠秀郎满身。
他骤然止步,一掌推回。
刀雪倒泼,才在空中勾勒出英武將军的身影。
大荆帝国绣衣郎將宫维章!
他隨手一刀,割开了戏相宜身上的束缚,昂首注视著对面的鼠秀郎。
“这声『抱歉』,我习惯听人族来说。我可以听人族作为胜者的反思,听不得异族突然泛滥的怜悯。”
宫维章抬起那柄魁刀,眸锋冷冽:“原来是你啊……鼠秀郎!”
鼠秀郎將目光从戏相宜身上挪开,看向这锋锐无匹的年轻人:“你认得我?”
san josesan josedating
这一切来得太顺利了。
刚窥见墨家的秘密,拿下【非命】这具极有价值的傀儡,捕获戏相宜这个机关天才。又等到宫维章亲来。
曜真神主身死的反噬,已经清晰体现。神霄天意是有偏向的!
当然曜真神主若是还活著,妖族能做的更多。
宫维章冷峻地道:“如果连妖族已经出战的绝巔都认不全,我也不配来经营神霄。”
手下瞬间灭了一旗,身为霜云城荆军主將的他,岂能不至。
当然一开始他预期的对手,是海族真王念奴兴。
在太平山归途反杀这尊海族真王,抑或在青瑞城反杀,没什么不同。
本来借洞天宝具潜来,是要毕全功於一刀。在探知目標远超洞真强度后,他是不打算动手的。
但戏命竟然在这里体现绝巔战力,其本身又是一尊傀儡!
戏氏兄妹身上所藏著的墨家巨大隱秘,绝不能落入妖族手中。
所以他不得不横刀於前。
当然相关的求助讯息已经先一步发出,但囿於两重天境当下趋於稳定的对峙形势,双方绝巔强者都不似战爭前期那么容易调动,牵一髮而动全身……他需要爭取一段时间。
鼠秀郎踏步而前,眸色泛冷:“区区洞真境界,杀你有失身份。滚吧!这里没有你的事!”
他求杀宫维章而不言此,好似真心只想赶走这人。
以绝巔谋洞真,仍然如履薄冰,求万无一失。
非他秉性谨慎,事实上他经常发疯……但为妖族大事,不敢轻率。
“这里是荆国治下霜云郡。本將奉旨镇守,当佑此地一切人族安全。”
宫维章不避反前,竟然主动向鼠秀郎走!
“鼠秀郎,你在这里拔刀,那就是我的事。”
面对妖族大圣鼠秀郎,他闻名则遁。面对於神霄重构绝巔的天妖,他望风而逃。面对一个一年前死里逃生,而今消耗巨大,已为绝巔戏命所伤的半残对手……
洞真境的盪魔天君会退吗?
今日未尝不可提子屠龙!
已经斩开束缚的戏相宜,跪在戏命的残躯前,本能地想要修补什么,但又不知从哪里修起,双手不知所措地张著。
披甲的宫维章,將这对兄妹护在身后,提刀踏步,身如薄刃切风!
鼠秀郎大张五指,虚按地面,妖异白焰周掠而飞,已经將整个戏府圈为禁地。
天空仿佛下坠,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。漫天飘雪,落肩极重。此为滯法之地,將阻绝一切逃脱手段。
他这才放心与年轻的人族天骄对杀:“什么事都要往肩上揽,那就看看,你担不担得起!”
“中央月门战场,计太师放你一马,你不思侥倖,不知道藏回老鼠洞里,还敢拋头露面!”
宫维章迎风劈雪,势不可挡,像一柄无所畏惧的刀:“这个遗憾,就让我来弥补!”
就在斩刀將近的瞬间,他横掌在身前一按——
无形的力量自他掌心漫延,推开一层巨大的涟漪,將他和鼠秀郎都框束在其间。
<iframe width=“100%“ max-width=“300px“ height=“100%“ max-height=“250px“ sandbox=“allow-forms allow-pointer-lock allow-popups allow-popups-to-escape-sandbox allow-scripts allow-same-origin“ frameborder=“0“ scrolling=“no“ marginwidth=“0“ marginheight=“0“ srcdoc=“&lt;body style=&quot;margin:0px;&quot;&gt;&lt;!-- adwheel / bn_exo_300x250_entertainment_torrents_na --&gt;
&lt;ifra
' scrolling='no' style='margin:0px; border:0px;'width='300' height='250' allowtransparency='true' frameborder='0' framespacing='0'&gt;&lt;/iframe&gt;&lt;/body&gt;“></iframe>
俄而流光织线,天地拔笼。
他和鼠秀郎进入一座坚不可摧的战场。
洞天宝具……【画牢】!
由三十六小洞天里排名第十九的“长耀宝光天”所炼,是荆国歷史上那位不得不死的魘神鄢华川所遗留的宝具,因鄢华川之死而尘封。
许多年养炼,已重现昔日威能。
荆天子特意將之赐下,就是为了確保宫维章在神霄世界的安全。倘若蒋肇元见到它,当知宫维章之重,是断不敢再有什么不满的。
此宝有两个能力,一为“画”,一为“牢”。
“画”可以速写敌情,是探查手段。“牢”则坚不可摧,是一眾洞天宝具里,囚敌第一的宝具。
鼠秀郎要把他留在这里,他也要把鼠秀郎留下——遂画地为牢!
锋锐绝伦的人族天骄,和美丽危险的妖族大圣,消失在漫天飘雪中,隱为雪下虚悬的那一圈光轮。
这是一场只覆盖了戏府的雪。
带来戏相宜永不能忘的冬天。
她抱著只剩半躯的戏命,眼泪冲刷著油彩混淆的花脸,微张著嘴,但没有哭出声音。
这该是一个平静的午后,她沉浸在自己的灵感世界,快乐地创造一些奇妙物件……机关室外的一切都应该与她无关,从没想过要如此仓促地迎接命运。
可“仓促”,正是命运到来的方式。
戏命就是【非命】,戏命只是傀儡。
她曾作为墨家的天才少女,主持【明鬼】的维护和驾驭。
她清楚地知道,【明鬼】並不具备感情。那只是一块铁,一堆木头,一具冰冷的造物!
但为什么还这样难过呢?心口好像被什么堵塞著,其间不得脱出的洪涌,像重锤砸击著心门。
戏命不说话,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,静静地看著她。
这是最后的注视。
属於【非命】的命能已经消耗一空,即便没有鼠秀郎给予致命伤害,强行开启第五態的他,也本就要走向毁灭。
因为他只是一个未完成品。
是一个失败的造物。
“呜呜呜……”
“哇啊啊啊——”
戏相宜从来只在机关术上敏锐,除此之外,做什么都很迟钝。就连悲伤也想不明白,就连哭泣也迟缓很久。
直到这时才哭出声音。
她从来没有哭泣过。她的哭泣像是一个孩子那么无助,嚎啕著想要父亲母亲带自己回家。
可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,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。
她只有一个哥哥。而哥哥戏命就要死了。
“不要为我流泪。”
戏命伸手想要为她拭去眼泪,可断肢只剩半截只是无力地弹动了一下,滋滋滋,早就崩溃的阵纹,进一步被鲜血蚀毁,又咔咔咔,发出零件碎裂的声音。
他只能看著戏相宜,这是世上最遥远的距离。
“我不是你的兄长。我只是一首写给你的情诗,写我的人三百年前就已经死去。”
“真正爱你的人,是饶宪孙。”
“你是他的孩子。”
是啊,一个傀儡所表现出来的一切,都是机关师的赋予。
一个傀儡所表达的爱,当然出於机关师的心。
这个世上没有人爱戏相宜。因为今天爱她的是傀儡,三百年前爱她的是死人。
戏相宜的眼泪停下了。戏相宜的伤心停不下来。
她救不了怀里的这具傀儡,她修补不了她的心。
最后她也看著戏命的眼睛,她问:“你是自愿,还是受到强制的命令呢?”
在妖界的时候,戏相宜曾经问过——
“傀儡无保留的付出,算不算真正的爱呢?”
那时候戏命回答——
“根据过往经验的总结——想来爱是自愿的付出,不是强制的命令。”
现在戏相宜等他的答案。
而他的眼中毫无波澜:“我只是一个傀儡。”
傀儡並不懂得如何去爱,所以不要为傀儡伤心。
傀儡坏了就再做一个新的,旧的机关总是要被时代淘汰……你这么天才你应该懂。
戏相宜抿著唇,只是紧紧抱住了戏命的残躯,在雪中再也没有声音。
“我的酒呢?我的求道酒……”
戏命的喃声被绞碎在咔咔声响。
他的酒已喝光了。他的生命已走到尽头。
“我的【神天方国】告诉我,它更接近水的构成。但我喝它的时候,总有微醺的感觉……我想它是很好的酒。”
他的眼睛黯下来,其间的璨光都散去。
像是吹灭了灯。
感谢书友“甘木线”成为本书盟主,是为赤心巡天第1036盟!
感谢书友“屿岁”成为本书盟主,是为赤心巡天第1037盟!
感谢书友“窃书一小贼”成为本书盟主,是为赤心巡天第1038盟!
感谢书友“落羽神都”成为本书盟主,是为赤心巡天第1039盟!
……
下周一见。
(本章完)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