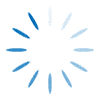周末,久未休息的徐安终于可以安稳地躺在床上,享受一个没有回测和交易的周末。
厚实的窗帘隔绝了阳光,房间里一片昏沉。窗外有风吹动树叶,发出细碎的声响。她抱着枕头,陷在深沉的睡眠里,直到手机振动,将梦境生生撕裂。
屏幕上闪烁着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——俞景。
短短两个字,像被锋利的刀刃划开,翻出了她来纽约这么久被刻意遗忘的疼痛。短信只有一句:
我带孩子来纽约玩,愿意见一面吗?
她的心猛然一紧。
她匆匆忙忙洗漱完,披上外套就跑出了门。中央公园林荫道的入口,人声嘈杂,阳光晃得她睁不开眼。远远的,俞景拉着小孩,冲她挥手。
那一瞬间,徐安觉得眼前的世界失了焦。只是几个月的分别,却模糊得好像隔了半生。
她的前夫,俞景,是一个很纯粹的人。明亮,耀眼,但是纯粹。纯粹到她见到他的第一眼就爱上了他。
那个时候她刚和魏锋分手,带着一些无处安放的迷茫,从纽约回到新泽西。为了散心,她去听了高等研究院的一场量子场论讲座。演讲的就是俞景。
他讲标准模型,讲量子场的重整化,讲规范对称性如何约束粒子的相互作用,讲弦的震动模式如何决定宇宙的谱系。他在讲台上侃侃而谈,像是在描摹一幅宏大的宇宙蓝图,黑板上密密麻麻的公式像是暗夜里闪烁的星河。
她突然觉得通向更大世界的门被打开了,她看到了数学规律在宇宙中的应用。那些她日复一日推演的复杂而抽象的数学表达:希尔伯特空间、李群,突然都有了现实的归处。一条原本静默的数学长河,被物理的光辉点亮了。
阳光从窗外斜射在讲台上,他的侧脸分明得像白纸上的铅笔线条。那一刻,她毫无预兆地坠入了某种热烈而危险的黑洞里。
后来,他们在图书馆偶遇,在食堂点同一种咖啡,在樱花树下并肩走过。故事顺理成章地发生,一如所有烂俗的爱情故事。
其实徐安也不知道一切是怎么走到不可挽回的地步的。俞景并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爸爸,他会在夜里第一个醒来喂奶,会换尿布,他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留给了徐安和小孩。但徐安,仍然不可抑制地感觉到了生活的失控。
她一边恢复身体,一边准备博士答辩,却总被孩子的哭闹牵扯得筋疲力尽,思绪不再如往昔清明。终于熬到托儿所排上了名额,她以为可以回到数学世界,却迎来了那份诊断结果——重度自闭症。
徐安已经不记得当时的感受了。只记得那天晚上,屋里只开了一盏台灯,她和俞景坐在沙发的两端,沉默得连呼吸都显得刺耳。过了很久,他走过来抱住她,低声说一切都会过去的,他们一起面对。
但她知道有些痛苦是过不去的。
俞景提议他可以辞职,在家带小孩。那个时候他刚拿到助理教授的职位,正是忙到天昏地暗却薪水微薄的时候。
徐安想到了她刚见到俞景的那天,他在台上讲量子场,讲大一统,像点亮世界的光。俞景其实是一个很纯粹的人,他毕生所求不过物理。她不想他失去眼里的光。她拒绝了他的提议,选择自己在家里带孩子。
但是徐安自己呢,她在数学世界里求得的那一片安心之所呢?
之后的六年,漫长得像无止境的隧道。徐安就这样熬了六年,每天面对着大喊大叫蛮不讲理的小孩。她耐心地照顾他陪伴他,内心里一天天数着日子。
她的世界缩小到只有育儿、康复、和无尽的等待。每天深夜俞景回家,会看着好不容易安睡的小孩和她讲物理,讲最新的学术进展,但是徐安的世界已经小到容不下那些抽象的公式了。
他不是没有察觉到。有时候他会整夜的失眠,在小孩醒来的第一刻将他抱起,只为不惊动她。他知道她在远离,却无能为力。他不能失去物理,也不能失去她。
徐安有时候想,像俞景那样的人是应当孤独终老的,而不是背上了婚育、责任、柴米油盐后,仍然云淡风轻。
可偏偏,徐安爱上的就是这样的俞景。
终于,有一天,俞景怀揣着满心的喜悦回家,告诉徐安他拿到了终身教职的好消息。小孩也终于等到了政府安排的干预老师。
俞景抱住徐安,感谢她的付出,告诉她接下来自己会承担更多,她终于可以自由一点了。
徐安愣愣地听着,指尖还粘着切菜的水珠,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:要记得把小孩的资料整理好,明天交给老师。
那一刻,徐安突然意识到,她已经失去幸福的能力。
六年太久了,久到她已经没有办法在这样的日子中品味到丝毫的幸福,久到对于美好的未来她不是期待而是疲惫,久到面对依然耀眼纯粹的俞景她不是爱慕而是抑制不住地恨。
凭什么呢,凭什么我们两个人共同孕育的小孩,却只有我一个人被困住了。
爱、热情、希望、对世界的好奇心,这些曾让她燃烧的东西,早在不知不觉间被耗尽了。
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孤独,像溺水,像在黑暗里无声地挣扎,没有人能听到她的绝望。
所以,徐安决定离开了,把俞景和小孩都丢下。
她提出离开的那天,第一次看到俞景哭。他缩在沙发里,头埋在手掌里,像是猝不及防,又像是早有预料。他的肩头耸动着,无声无息地流泪。等到眼泪流尽的时候,他终于抬起头,满眼通红,却只是说:“你走吧,我会照顾好小孩的。”
徐安又想起了初见他的那一天,洒满讲台的光,写满黑板的公式,他神采飞扬。他说:“细推物理须行乐,何用浮名绊此生。”
那时的她年轻,天真,以为数学与物理就是他们将要携手度过的此生。
一阵风从林荫道吹过,带着初秋草木的气息,把她从失重的回忆拉回现实。她抬起头,看见俞景正拉着孩子向她走来。
孩子比记忆里高了点,瘦瘦的,身子微微蜷着,低着头像在躲避光。指尖反复搓着衣角,脚尖一下下地蹭着地面,像是在用重复的动作将世界维持在他的节奏里。
徐安走近,停在三步开外,目光从孩子细瘦的肩膀上掠过,落在俞景身上。几个月不见,他瘦了很多,眼眶深陷,眉宇间压着疲惫。但看向徐安的时候,他的眼神亮了一瞬,仿佛来自旧时光的光重新翻涌出来。
徐安的目光又落回到小孩身上:“他……比以前高了。”
俞景顺着她的目光,轻轻拍了拍小孩的肩膀,语气里带着小心的骄傲:“是啊,他最近长得很快。”
孩子忽然抬头,眼神滑过她却没有停留,像不认识她一样,只盯着她身后的一片飘落的叶子,声音忽然尖锐起来:“叶子!叶子!叶子!”
徐安的喉咙微微收紧,那种熟悉的无力感又回来了,心口像被什么堵住了。
“我们走走吧。”俞景忽略了吵闹的小孩,声音温柔得几乎被风吹散。
徐安点头,两个人并肩而行,彼此间却始终隔着半步微妙的距离。
“工作还好吗?”是俞景先开口。
“嗯。”她顿了顿,“我转给你的钱收到了吗?”
“收到了。”他低声说,“你转得太多了,我和小孩不需要那么多的。”
“拿去请人照顾他吧,你一个人太辛苦了。”
“好。”
公园的湖边有一排长椅。他们坐下,小孩没有看他们,却悄悄地缩在徐安的身边,像一只需要安全感的猫,紧紧握着一截不知道从哪儿捡来的树枝,机械地,没有节奏地敲击着长椅的扶手,邦——邦——邦。
徐安看着湖面,正午的阳光在水波间碎成无数细小的光点。她眯了眯眼,开口问:“你们什么时候来纽约的?”
“昨晚到的,怕打扰你休息,所以今天早上才联系你。打算后天走。”
“你们住哪儿?”她的视线依旧没有离开湖面。
“法拉盛的民宿,城里太贵了。”
“还是住到曼哈顿吧,我给你们订酒店。”
俞景低下头,像是怕她看见他眼底的波动。他轻轻抱起孩子,语气刻意的轻快:“妈妈挣大钱啦,要请我们住酒店呢。”
徐安看着他们,嘴角轻轻扬起。
“徐安,好久没有这样了,和你在一起。”俞景转头看向徐安,声音低而温和:“真好啊。”
风从湖面吹来,带着湿凉的水气,吹乱了她鬓边的发丝。
徐安沉默了片刻,才像是用尽了全部力气般开口:“俞景,我又结婚了。”
俞景的指尖在膝盖上蜷了一下,像被细针刺到,又很快松开。他慢慢抬头,眼睛里有短暂的空白,眼圈一点点泛红,又被他极力压了下去。
湖面被风掠过,水面泛起细细密密的涟漪,阳光裂成的碎片像不经意的刺痛。
许久,他终于开口,声音几乎融进风里:
“希望这一次,你能幸福。”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